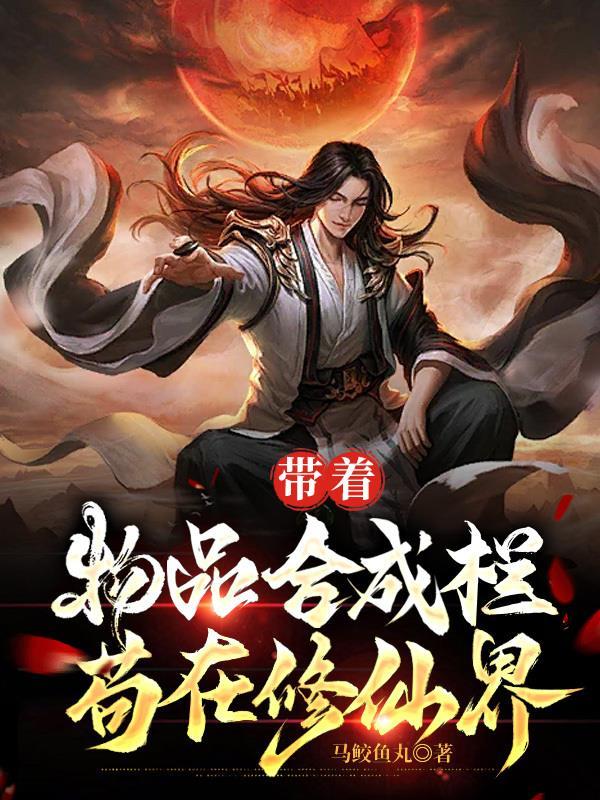小燕文学>九锡 > 第877章 875圣人之道(第1页)
第877章 875圣人之道(第1页)
父子二人来到太华池畔的八角亭,景帝坐在宫人们提前准备好的藤椅上,乌岩则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聆听训示。
他似乎还没有从先前激荡的情绪中抽离出来。
不怪他如此失态,毕竟二十多年来,景帝在他心里的地位比高山更高,敬畏之心压过一切,说一句噤若寒蝉并不为过。
今日骤然听到景帝那句满含期许的勉励,乌岩险些当场掉下眼泪。
景帝看了一会秋日阳光下水面上的涟漪,平静地说道:“这大半年你很用功,朕都看在眼里。虽然有些时候你的处事手段略显稚嫩,但是至少你有上进的心思,这便是可取之处,所以朕对你抱有期望。眼下你即将监国,朕便考考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乌岩好不容易平复的心境猛地紧张起来,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宏大,而且让他当面评说帝王之道,这显然有些逾越。
景帝见状淡淡一笑,抬手斥退周遭的宫人,道:“想到什么便说什么,朕不会见责。”
乌岩忐忑地思考着,小心翼翼地说道:“父皇,儿臣认为如果可以做到朝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应该就是有为之君。”
“你说的这些没有错,不过还有一个前提。”
景帝双手拢在身前,徐徐道:“你要能掌控手中的力量,才能让臣民按照你的设想做事。如果朝中吏治败坏,百官阳奉阴违,你要如何处理?如果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你要如何安抚?”
乌岩默然。
景帝转头看着他,似笑非笑地说道:“不听话的臣子便杀了,百姓敢造反就调大军扑灭,是不是这样?”
倘若治国真有这么简单,史书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亡国之君。
乌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诚挚地说道:“请父皇赐教。”
“其实这些手段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身为帝王要站得更高一些。”
景帝抬起右手高过额头,耐心地说道:“朝中吏治败坏,究竟是他们腐化的度太快,还是你身为天子赏罚不公偏听偏信。百姓竖旗造反,究竟是有人蛊惑人心煽动民怨,还是官员和贵族沆瀣一气荼毒百姓。你先要弄清楚生这些状况的缘由,而不是立刻做出武断的定性。为君者,最忌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它会让你变得愚蠢又短视。”
乌岩豁然开朗,敬服地说道:“儿臣明白了。”
景帝颔道:“知其源头,对症下药,方为处事正道。”
“是,父皇。”
“朕知道你身边有不少幕僚谋士,想来这大半年他们给你出谋划策,教了你很多权谋之道,不妨说说有何心得?”
乌岩有些迟疑,看着景帝鼓励的目光,于是老老实实地说道:“他们确实说过很多,儿臣闲暇时总结了几条。”
景帝微笑道:“说来听听,莫要害怕。”
如果没有先前和谐的气氛作为铺垫,乌岩根本不敢实话实说,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幕僚里肯定有父皇安排的人,于是鼓起勇气如实道来。
“第一是平衡之法,朝中官员和贵族难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结党抱团,无论哪朝哪代都无法禁绝,因此帝王绝对不能让某个利益群体一家独大,否则必然会威胁到皇权的安危。”
“第二是杀伐决断,所谓慈不掌兵义不理财,掌握权柄更是如此,心慈手软只会埋下无尽的隐患。尤其是对那些敢于窥伺皇权的人,务必要用鲜血和杀戮震慑一切宵小。”
“第三是威不可测,虽说揣摩上意是绝大多数臣子都会做的事情,但是看不透的人和事才是最可怕的,才会让那些人感到畏惧。倘若帝王的心思可以轻易被臣工猜透,那么他就很难真正控制朝堂。”
“第四是黑白相间,这世上既有精明老练的奸臣,也有迂腐昏聩的忠臣,奸臣不代表愚蠢,忠臣也不代表聪慧,品格与能力不一定完全对等。因此用人不能只看忠奸,还要注重他们是否能在合理的位置挥作用,并且要有随时罢黜他们的手腕。”
乌岩越说越流利,他注意到景帝的表情一直都很平静,于是恭敬地说道:“父皇,这就是儿臣大略的想法。”
其实他心里还有一个念头,这些手段都能从景帝的治政过程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只不过他终究不敢妄议君父。
景帝沉吟片刻,颔道:“你身边的文士倒也不算肤浅,这些心计便是所谓的帝王心术。乌岩,虽说你的天赋确实要比纳兰稍逊一筹,但你胜在勤奋好学且善于总结,假以时日便能愈纯熟,只要能做到言行合一,对付绝大多数臣子都已足够。”
乌岩心中一喜,面上不敢表露出来。
景帝端起桌上的茶盏饮了一口,平静地说道:“不过朕要告诉你,这些帝王心术不值一提。”
乌岩怔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