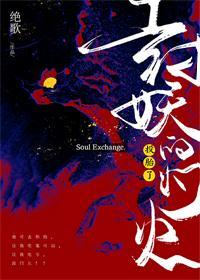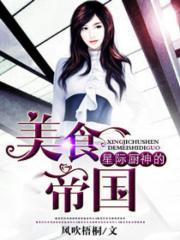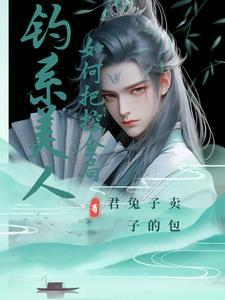小燕文学>四合院,人小鬼大谁见谁怕! > 第621章 决定回北大荒(第1页)
第621章 决定回北大荒(第1页)
当王建国决定前往医院的那一刻,他总是脚步匆匆,沿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街巷快步前行。
街边的树木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似在轻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可他却无心欣赏,满心都想着医院里的朋友们此刻过得怎样。
踏入医院那扇自动门,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瞬间将他拉回现实的沉重氛围之中。
他熟门熟路地穿过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人们的嘈杂声、小孩的哭闹声、广播的通知声交织在一起,却无法扰乱他前行的脚步。
他沿着略显昏暗的长廊一路走去,头顶的灯光散着昏黄的光晕,映照出他略带疲惫却又坚毅的面庞。
不多时,王建国来到了杨小花工作的科室附近。他放缓脚步,目光在人群中仔细搜寻,果不其然,一眼就瞧见了赵书卓。
只见赵书卓正如同一个忠诚的卫士般,守在一旁,忙忙碌碌地帮着杨小花做各种事情。
有时候,他会全神贯注地整理那些堆积如山、杂乱无章的医疗文件,将它们按照类别、日期细心归档,方便杨小花在繁忙的工作中能迅找到所需资料。
有时候,他又会主动承担起搬运沉重医疗器械的苦差事,累得额头上挂满汗珠,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后背,可他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毫无怨言。
再看杨小花,身为医护人员,身处这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每日面对形形色色的病患和纷繁复杂的病情,身心俱疲那是常有的事儿。
更何况,不久前她自己身上还有骨折的伤痛,那段日子,行动不便的她每走一步都要忍受钻心的疼痛,可即便如此,她骨子里那股坚韧不拔的劲儿从未消散。
如今,身上骨折的地方也好得七七八八了,她又重新活力满满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展现给大家的,依旧是那张充满朝气、洋溢着温暖笑容的脸庞,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一切都好。
她的笑容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能驱散病房内的阴霾,给每一位病患和同事都带去慰藉与力量。
然而,只要一谈及杨小花父亲的病情,气氛便会瞬间凝重起来。
当初,为了给杨父寻得有效的药物,王建国可是费尽周折,四处打听、奔波劳碌,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才好不容易觅得那珍贵的药源。
杨父用上药之后,病情确实暂时稳住了,没有进一步恶化,这让大家原本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可谁能想到,后续的展却不尽如人意。负责诊治的周大夫每次前来查房,都会带来令人揪心的消息。
周大夫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病房,身上的白大褂一尘不染,仿佛带着一种让人敬畏的威严。
他先是仔细地查看杨父的各项生命体征,眼神专注而专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
随后轻轻合上病历夹,微微摇头,脸上带着几分无奈与惋惜,开口说道:
“目前来看,只能继续观察了。这病棘手得很,咱们用上的药物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维稳作用。”
“可想要实现病情的明显好转,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得依赖病人自身的恢复能力。”
“当下,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密切留意病情的每一点变化,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周大夫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可在众人听来,却字字如重锤,狠狠地砸在心头,让那原本燃起的一丝希望火苗,又被阴霾笼罩。
王建国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周大夫的话,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
他将目光投向杨小花,看着她既要肩负繁重的医护工作,又要为父亲的病情忧心忡忡,眼眶不禁微微泛红,对她又多了几分心疼。
而赵书卓呢,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眼神中除了忧虑,更多的是坚定,仿佛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前路如何艰难,他都要陪伴杨小花走过这段风雨坎坷。
在董书记家中已经度过了好些时日,王建国每日忙忙碌碌,悉心照料着董书记的起居。
他看着董书记的面色从最初的略显苍白,一点一点地恢复了红润,眼中的神采也日益明亮起来,心里满是欣慰,估摸着董书记的身体已然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些天,他也没闲着,把董书记家里里里外外能想到的活计都干了个遍。
从清晨起来清扫庭院,将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帮着擦拭家具,让那些旧物件都重新焕出光亮。
又或是精心料理着阳台上的花草,浇水、施肥、修剪枝叶,让原本有些蔫蔫的绿植重新生机勃勃。
眼瞅着一切都步入正轨,王建国心里清楚,是时候该回北大荒了。
那里还有未完成的工作,还有等着他一起奋斗的战友们。主意既定,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便迈着大步前往医院去找赵书卓。
一路上,王建国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北大荒广袤无垠的黑土地,那片土地上春天播种时的忙碌场景。
夏天作物茁壮成长的蓬勃生机,秋天丰收时的热闹喧嚣,还有冬天皑皑白雪下的静谧祥和。
他深知,那是他的另一个“战场”,即便心中对董书记一家有着诸多不舍,但责任在肩,脚步愈坚定。
来到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王建国熟门熟路地穿梭在走廊间,眼神急切地寻找着赵书卓的身影。
他要亲口告诉赵书卓自己的决定,也想再听听这位老友对回北大荒这件事的看法,毕竟现在还牵扯到他和杨小花的事。
王建国迈着略显急切的步伐,穿过医院那略显清冷的长廊,长廊两侧的白色墙壁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有些刺目的光。
不多时,他来到了杨小花的病房门口。轻轻推开那扇半掩着的门,屋内的景象映入眼帘,出乎意料的是,赵书卓并不在病房之中,只有杨小花静静地坐在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