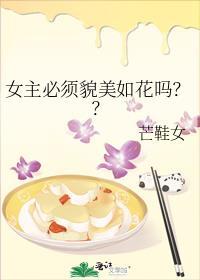小燕文学>战锤40k:碎裂钢魂 > 第449章 Project XI(第2页)
第449章 Project XI(第2页)
“但不包括对兄弟下死手。”佩图拉博说,开始怀疑鲁斯当年与十一号初遇的情况,他记得是黎曼·鲁斯最初汇报了十一号的行踪。
“我的确伤害了你的兄弟,你要斥责我,那你就做吧。”“不止如此。”
“你要用杀戮的数量论罪,我杀死的人不及大远征中一个最微小的零头——死亡和毁灭是它诞生的根基,你们之中最仁慈的人,都有意地饲养着它,何况洛嘉·奥瑞利安也在你们之中……”
“我要问的是你又用谁的血饲养出一条吞噬星辰的混沌巨蛇!”
金色文字组成的巨盾在刹那间消失,而后骤然放射出链状的线绳,结成一张硕大的网,将水晶蛇紧紧捆缚在内。
三头蛇在网中不断挣扎,剧烈地扭动着它那晶莹剔透的身体,试图挣脱这束缚。而莫尔斯所准备的咒言网罗则坚韧不可摧毁,不断向内收拢,水晶的蛇身喀啦啦地断裂,声响令人悚然。
巨蛇即刻开始蜕皮,以极快的度褪去旧壳,希望借此逃脱,而金色的网并未松懈,反而越收越紧,莫尔斯神情冷峻,他的黑袍边缘已经被分解成文字织的金色细线,在非物质的领域中折跃扩展。
很快,水晶蛇第二次蜕皮,它意图挣断巨网,或从缝隙中逃离,但所有的努力都无从生效。
佩图拉博注意到莫尔斯的脸上忽而划过一阵诧异,工匠迅更换了一些符文,在其中添加更多的附加作用,而他越是这样做,那份诧异就越明显。
他从窗边让开,将施法的空间完全留给工匠本人。
网与蛇的斗争迟迟未决,莫尔斯突然开口“谁改变了你的形态?”
+这就是我。+三头蛇压抑着被金网割伤带来的剧痛,蛇眼时而出现在窗外,与室内的佩图拉博直接对望,+这也是你,是你们中的所有人。为了——啊——+他的尖叫如同锋利的刀刃划过玻璃,而他的声音变得更轻,比吹过泰拉皇宫尖顶的第一缕风更轻,在宇宙之中仅仅稍大于无声的寂静。
+为了成为暴君星,父亲让我们诞生,又让我们遗忘我们最早的本质(essence),而我既然看见了,除了聊胜于无的伪装,就不再有退路可走——+佩图拉博在一个瞬息里归纳了他获取的全部信息,并立即组织语言,就像他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将他多重的惊讶统统抛之脑后。
“帝皇必定可以重新赋予你一个外形,十一!”
+那你要想办法阻止我,佩图拉博。+十一号的水晶外壳最后一次破碎,他舍弃的部分比先前任何一次都多,而这些硬质的外壳终于将莫尔斯的追击阻拦了片刻。一道残缺不全的流光坠入帷幕之后,将他原本栖居的星球伊士塔尔抛弃在真空中。
莫尔斯收回全部的咒文丝线,踉跄了一步。
“该死的尔达啊,十一号简直不怕死。”他骂了一句,并顺口更换了用于加强语气的词。
随后,莫尔斯甩了一下头,缓过劲“他的伤势不轻,希望下次见到他,他还能喘气——他吸收过多少亚空间能量!”
佩图拉博在原地站了片刻,告诉自己他该提问了,他并不害怕得到答案,并且他也应该得到它们。他知道如果自己问出口,莫尔斯就会回答,他也知道十一号透露的信息里存在一定的被隐藏的真相,因为在话语的背后,工匠正小心地端详他的表情,想看出他的心情和看法。
“那个亚空间造物就是十一号?”他说,声音不大也不小,就是平常的语气。他听见自己的问题在有限的空间里怪异地回响着,听起来并不自然,“那是——基因原体?”
“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莫尔斯刻意耸了耸肩,“你知道,这只是让你们的存在变得更传奇了一点。你总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纯人类,对吧?你就没这么认为过。”
在佩图拉博点头后,工匠继续说“看起来尔达解放——我倾向于通过某种形式使得十一号放弃了正常外形。如果洛嘉果真看见了一个人形的基因原体,那只能是他给自己穿的临时外皮。至少……他用这个更本质的容器形体存储的灵能量比马格努斯还夸张一档。”
佩图拉博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叹了口气“你告诉过我,帝皇是我的造物主。”
“有时候你也应该从字面意义理解,”莫尔斯说,“而不是自动代换成‘父亲’之类的,那是社会关系方面的概念。”
佩图拉博又静止了几秒,然后坐回他的椅子上。
他本应为这则消息惊讶,但他对这一点感受不到除理智之外的东西他的心被另一则暗示夺走了注意,仿佛一串古老的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想过的门,而那扇生锈的铁门明明就在那儿,只是他下意识觉得他们的道路一定在另一扇更宽阔的金门之后。
“光明会的目标是阻止暴君星的降生,这与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佩图拉博说,想起莫尔斯为他朗诵那封信时的未尽之言,“但假如——我们中的一部分知道,帝皇就是暴君星……”
“那么情况会变得十分复杂。”莫尔斯说,他的脸上增添了某种更深沉的,蜡质的阴冷,“有些人会过多地推动它,有些人将徘徊不定,而我相信也有人执意阻止。”
他顿了顿。
“帝皇不想告诉你们,但他的确决定了。‘也有一些人阻止暴君星诞生,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胆怯,而是出自对我过高的看重,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情感而阻拦我,即使我不会因此责怪他们。告诉佩图拉博,我卸任后,帝国将由马卡多与荷鲁斯执政,而你与佩图拉博将前往暗面的网道。’这一部分显然不是用来完整地读给你听的,佩图拉博。”
“所以,父亲会……”佩图拉博感受着自己的情绪,这是什么?惊讶吗?还是不舍呢?或者说恐惧,久违的恐惧?还是一种尘埃落定的茫然?他想起帝皇,接着他继续说“……走向终结?”
“他已经走在路上了。”莫尔斯回答。“我的建议是,我们去伊士塔尔看看,说不定能把尔达找出来。我决定让她停止继续仅仅活在我们的嘴里。”
——
“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
洛嘉背诵着今日的经文,重复着不知道第多少轮的通读和默诵。他的任教团长常常被他记忆而起,因此今日轮到了他从中获名的那一本书籍。
他此时所在的行星气候温和,和风煦煦,晨间的牧场里弥漫着浅淡的橄榄香,正是今日心烦意乱的怀真言者所需要的——怀言者大军偶然至此,而当地人立即归顺。他将其视为祂怜悯之下赠予他的安慰。
他闭目漫步,让听觉和直觉指引他的路。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异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他脚下一顿,听见另一阵脚步声。衣袍翻卷,几个当地人正脚步轻快地向他跑来,这也是常有的事。他们今日带来了什么?花环吗?还是橄榄枝呢?
洛嘉睁开眼睛。
本章完